
我的目標就是徹底戰勝麻風病

很多人問過我,當初已經離開祖國那么多年,為何選擇回國?我都毫不猶豫地告訴他們:因為我是中國人,我在北京出生,不能忘本。
當時的新中國還在成立初期,一切都百廢待舉,正是急缺人才之際。我曾在美國時代雜志封面上看到過我國導彈專家錢學森,當知道他毅然回國的消息時,內心有著很深的觸動。那時的我已經三十多歲,時不我待,作為中國人,我很渴望回到祖國的懷抱,想把我最好的年華奉獻給祖國。
1978年,我接到國家交給我的任務,正式就職于北京熱帶醫學研究所,從此和麻風病防治研究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。這項工作于我而言雖是嶄新的研究領域,但麻風病卻是人類所面臨的古老疾病,被認為是“不治之癥”,因病致殘的麻風病人也一直備受歧視。過去世界上很多麻風病人被隔離就算是好的,不隔離可能就面臨著被活埋、被燒死、淪落到無家可歸等情形。因此,說起麻風病,人們往往談之色變,深入工作中,我也深感麻風病人遭受的疾苦。
記得1979年到云南省的麻風村做實地考察時,我見到了好幾個年輕的麻風病姑娘和她們深受病痛折磨的家庭。她們本能夠擁有青春的年華和幸福的生活,但身心每天都遭受著痛苦與折磨,眼神里也透著絕望。但當時的麻風病防治工作還只注重實驗室研究,研究成果往往不適用于實際,而根據前期積累的大量調研數據,我深知只有深入到病人身邊、進行非隔離治療現場研究,才有可能解病人之疾苦、消社會之歧視。
上世紀八十年代初,在西雙版納勐臘縣境內麻風寨的麻風病防治研究工作開始了。我們皮防站的兩位同志在全縣范圍內歷經三個月的艱苦考察,探訪到的都是禿手禿腳、老鼠咬了手腳都察覺不到、生產生活不能自理的晚期病人。這不僅使我們工作人員內心受到極大震撼,同時大家也決心要治好這里的病人。隨之,我也把有關中國麻風病情況的詳細報告遞交給世界衛生組織,最終得以實施麻風短程聯合化療項目,并收到了世衛組織援助的聯合化療藥品及車輛等物資。
1983年初,短程聯合化療現場實驗正式施行。實際上,在村民們的固有觀念中,麻風病是治不好的,連村長刀建新也對治愈麻風病表現出極度的不信任。但在我們挨家挨戶為病人檢查潰瘍、耐心講解治療工作之后,尤其是刀建新,由強烈排斥逐漸轉變為接受。之后,刀建新還主動協助我們做通了村民們的思想工作,努力勸說大家服藥接受治療。服藥的過程并非一帆風順,新藥剛吃上二十幾天,有些病人的臉部從發紅到發紫,由于藥物副作用引發的恐慌,使有些病人開始拒絕服藥,甚至直接把藥扔進水里。面對大家的質疑,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再挨家挨戶做病人工作,告訴他們這僅是服藥后色素沉淀的正常反應,然后開導并鼓勵大家堅持服藥。三個月后,病人的色素沉淀明顯好轉,心理上的恐懼徹底打消,身體狀況也慢慢得以好轉。兩年后,我們為村民進行復查,結果顯示服藥病人全部治愈且沒有復發情況。
階段性的成果總是令人欣喜,但麻防工作不能停下。我經常對身邊工作人員說:“工作不能怕苦就不做、怕臟就不做,這不做那不做,我們身為醫務人員的使命何在?”當時我國的云、貴、川等地依然是麻風病流行的重災區,在國家和世界衛生組織的大力支持下,這些地區都相繼開始推廣實施短程聯合化療,短程聯合化療工作得以大力開展。而在這30多年深入基層過程中,7個地州59個縣的1萬多名病患得到治愈,麻防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。現如今,全國麻風病人從11萬人降至不足萬人,年復發率僅0.03%,遠低于國際組織小于1%的標準。
昔日麻風寨的村民已經過上了幸福的生活,我由衷為他們感到欣喜,同時也為從事麻風防治工作的人們感到自豪,是大家用堅持和奮斗給予了麻風病人新的希望。愛國有道,行為有范,艷陽與陰雨,平坦與坎坷,都是對我們工作的最高獎賞。
不忘初心、牢記使命,在多年的醫療工作和社會生活中,正是在黨和國家的大力培養、支持和幫助下,我們治好了很多患麻風病的老百姓,得到了全世界的承認,而且我們的治療方案也獲得世界衛生組織的認可,取得了一定的成績。隨著黨和國家在醫療衛生事業上,不斷加強對麻風防治工作的重視以及加大對防治經費的投入,當前我國麻風防治工作經驗豐富、成效顯著。這讓我看到黨和國家是真真切切在為老百姓辦實事、謀幸福,同時我也很感謝黨和國家,是祖國這片沃土造就了我,讓我有機會放手從事麻防工作,讓我有機會看到被治愈病人臉上洋溢的笑容、過上的幸福日子。
現在的我雖即將進入期頤之年,但不愿余下的日子在閑暇時光中浪費掉。在崗位上繼續奮斗、為老百姓辦實事是我應該做的,對于徹底戰勝麻風病,我做的還遠遠不夠。只要我不是醫院工作的累贅和包袱,我還愿意繼續工作,還愿意為麻風病人服務,我的目標就是徹底戰勝麻風病。因此,我會再接再厲,為黨和人民努力工作到100歲!


 微博
微博 微信
微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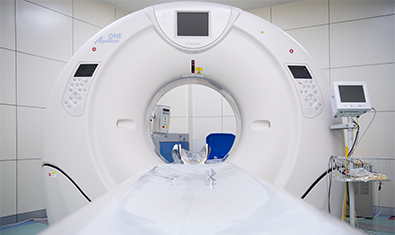
 京公網安備11010202008305號
京公網安備11010202008305號